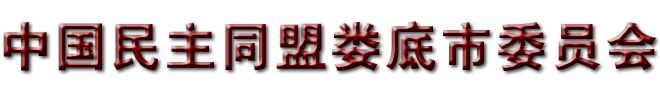古橋 古路與禁碑
我喜歡往鄉下跑,一來因為我是鄉下人,二來因為鄉下有著讓我魂牽夢繞的鄉土人情。
先說古橋。在鄉下,有水的地方就有橋。我見過大大小小、有名無名的古橋不下100座,木的,石的,大江大河的,小河小溪的,山溝的,平地的,各具特色。在婁底,資水流域、漣水流域的橋最多,以新化山區和楊家灘最有代表性。
新化山區的橋帶有明顯的苗瑤風格,保存完好且年代久遠;楊家灘的橋以清代為主,數量多,小橋多,簡單大方。每座橋都有一段艱辛的歷史,一個感人的故事傳說和一位令人肅然起敬的糾首,它就是一本書。
新化的油溪橋,修于清乾隆十二年,傳說是當地兩位鄉紳為首修建的。橋竣工時,兩位鄉紳的資產也用完了。修橋前,這里有渡無橋,一到汛期,從中游奔瀉而下的洪水像脫韁的野馬咆哮、洶涌,經常船毀人亡。也許是動了惻隱之心,也許是方便別人也方便自己,兩位鄉紳挺身而出,接著
沿著油溪橋辰光大壩向上走10來公里,有一座建于清道光年間的保存完好的全木質侗族式風雨橋,這是當地出身的五品官員和另一位鄉紳聯手捐建的。據碑文記載,從明崇禎年間起至清光緒的300年里,這里一直為水患所害,橋也屢建屢毀。這次,五品官員下定了決心,請來建橋高手,利用河中
嘉慶年間,在新化縣文田鎮,
保親橋全長
當年的榮華富貴、紛繁世事都化作了煙云,只有母親的善舉穿越了時空,與山川同在。
每當看到這些橋,我都要懷著虔誠的心,用腳丈量它們的長度,用手摸摸石頭、木樁或上面的雕刻,仔細閱讀碑文,或坐或睡到橋上,不肯離去。是的,那份不求聞達、不求感恩的道德自覺最終都化作了這些橋石和木柱,在歲月的磨蝕中越發光亮。我要感受那份久遠的感動與激動,一直到喉嚨好像被堵,淚眼模糊。
來到了楊家灘,大大小小的石橋讓人目不暇接,不禁讓人想起“花花綠綠楊家灘,把把戲戲南岳山”的歌謠。這里的橋有個特點,糾首要么是名門望族,要么是權貴功臣。這個商貿古鎮的富商以及“打開南京發洋財”的湘軍將士們,用智慧和生命換來的財富在家鄉大興建設公益事業的攀比之風,一大批以姓族為號的橋、路、祠堂、學堂如雨后春筍綻放在這塊人文薈萃的寶地。其中,6個寡婦集資修橋的故事傳為美談。有人說,將楊家灘的座座橋連起來,就成了楊家灘的家族史、發展史。
除了古橋,讓人流連忘返的還有古路。婁底人現在最痛惜、最難忘的是新化城關鎮的青石街。其實,古時的主要通道都是青石板鋪就的。新化縣圳上海龍有個村,至今村里有
在資水邊的纖道上,在漣源古塘去新化的通道上,在漣源株木去古湘鄉的山道上,都有記載捐資修路的石碑,都有溜光圓滑的青石。面對青石,直想用手去撫摸,用臉去貼近,光腳去踩或席石而坐。是啊,把抬青石上山的人和踩過青石的人串起來,就是我們的社會史、文化史。
今天,放眼一看,古路大多被毀,而古橋雖不多卻仍有不少依然屹立。是古橋構件不可拆卸和古橋有著民間認同的不可褻瀆的威嚴,或是其他什么,我已找不到確切答案。我只知道,在民間,架橋修路都是蔭及子孫的積德事。
是誰拆了古路?那個撬起青石板往家搬或往其他地方挪的人絕對不是修路人或修路人的子孫,他絕對沒有聽到“一、二、三”的勞動號子,沒聽到汗滴到石頭上的聲音,沒觸到肩膀上的繭和腳底的血泡……
我想到了禁碑。古路上都有禁碑,內容豐富。油溪橋纖道上的禁碑:“不許窩藏匪類,不許雞鴨踐食五谷,不許賭博,不許擔柴出外、鳧鴨入境。山林不許挖蔸混砍,冬青不許亂砍,稻草不許亂拖,不許酗酒打架,船戶不許赤身而過,桐子重陽后打,秋熟后瓜果包谷不許入畬,棉花要緊必定期,
坐石鄉風雨橋旁禁碑:“禁止藥毒河魚。國稞不許拖欠,煙館不許開設,不許吸煙,不許賭博,不許當賊贓……”
圳上有塊在井邊的石碑:“禁止在井里洗菜、洗衣。”
這些禁碑幾百年來都沒被毀,用今天的話來說,它包括了講文明、講禮貌、講科學持續發展,反對浪費。看來,這些禁碑曾經不僅是一塊石頭而已,它和鄉規民約一道維持著當地的社會生產秩序,神圣不可侵犯。
河水照樣在靜靜地流淌,村里的人們生生不息,一些老人甚至從沒走出過大山。走在橋上的我,依然能讀出先民們對大自然的敬畏與感恩。你看,哪一座古橋、哪一條古路不是天人合一,天時、地利、人和的杰作?
都說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但如果我們的家園沒有文化定力,最終會是泥沙與珠寶俱下。就是有珠寶沒被沖走,也會被淹沒在世俗的眼光里。什么時候,這些珠寶的光輝照亮著我們的胸膛,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就要到來了。
當前,是個欲望膨脹的年代,太多太高的欲望讓我們忘記了自己是誰。我們要經常給心靈放假,去鄉下走走看看。或許,我們會慢慢找回失落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