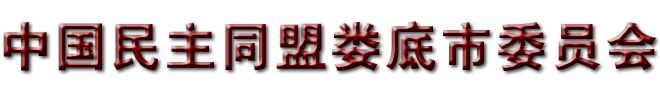我的故土之痛
父親感冒20多天了,還沒見好,他要我去尋一副草藥試試。我扛上鋤頭與叔走進了近20年未曾踏過的田坎土畬。初冬的故園,到處雜草叢生,深比人高,除幾塊精耕細作的田土外,其余從坳上到坳底,要么光板一塊,要么荒草一塊,長滿冬茅和鐵石爛(一種可穿破鐵石的草)。我的心被草堵住了,兒時背著背籃四處尋草,遇到一片稍密的草如獲至寶的那份激動,如今變成了壓在心口的石頭。因為到處是兒時千尋萬尋的草,叔在一邊嘆息著,指點著哪塊是張五嫂家的,哪丘是三粒子家的,都荒了好幾年了,只能用挖土機才能挖動了。唉,八十歲的人了,我也不想做了,但隔一年不做,他們打工回來,就挖不動了,土也不肥了,沒辦法,只有挖。一個不足1200人的村莊,初步估算,荒掉的田和土加起來有600多畝。大家耕作的是離家門口近的那些,離家1公里的統統荒掉了。
住在山腰上的二姐在小鎮上買了地,起了房子,農忙時回到山里勞作幾天又來到了鎮上,山上的十來戶人家陸續往山下移。當我問到山尖嶺上的土怎樣時,她說,全荒了,后來退耕還林了,只有4到5年的光景,除了門口的小部分田土外,其余也都荒了,都不想做工夫了。
家門口那口承擔本村和下村蓄水灌溉任務的大塘,干得要見底了。兩邊塘底上什么都有,爛衣服、玻璃瓶、石塊、塑料袋……還是70年代清過塘泥,里面八口活水井都被堵塞,塘壩被融蝕1米多,兩邊石墈只留下泥部淺淺的2層石塊,現在土墈實際上是田泥垛起的,融進了1米。流向下村的水渠,兒時我們在里面捉泥鰍、舀魚,現在水渠兩邊腫脹了,像腫了眼的人瞇著的眼睛,看不出水路。
我跟爹說:怎么不湊點錢修一下呢,他嘆氣說:唉,要他們出錢,他們寧肯讓它(塘壩)爛!私人的東西都不在乎,還講公家的!
柳嬸說,村里50歲以下的人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在三角坪打牌,沒人愿意干農活。20多戶人家中,只有2戶喂了豬,50%的人種了自己的田份,插一季稻,只要能維持家里口糧就行。40%的人要買蔬菜吃。
柳嬸抱怨說:“以前大家吃完飯,說的是‘做工夫去’,現在是說‘打牌去’,你也只講打牌,她也只講打牌,雖然不愁吃穿,但終究不是好事,你也不做菜,她也不種田,哪里來呀?”
晚上,四周漆黑,周邊五棟房子都沒人住,最近的一棟堂屋頂已塌了下來,他們都搬到其他地方去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著,失落注滿了心頭。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經濟富裕了的故鄉,讓我越來越陌生了。有很多好東西,有意無意中丟失了,再也找不到了。
記得1981年田土分到戶,近60歲的爹帶著我們三姐妹砌石墈,打百年基業,說這塊土可得多少豆子、挖多少紅薯,那塊土打多少麥子。可就是短短的3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田土變賤了,很多果蔬土種消失了,良種、轉基因、激素、農藥、反季節果菜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安全……
土荒了,田荒了,田變成土,也荒了。老人嘆息:作陽春劃不來啊!水利設施還是60年代建造的,山塘、水塘的蓄水能力很差。凡是要抽水的田都沒有人耕了。在家鄉,一個青壯年農民,打一天零工就有80-100元,能買1-2包米,可夠一家子吃上半個月甚至1個月了,年輕人已不想也不會作田土了。婦女們打麻將放一炮,就有近50元,也能買一包米了。只有那些上了50歲、沒有其他手工藝的人們堅守在田園上。
一邊是大量的田園荒蕪,荒草連天,一邊是麻將桌邊成群的人們,他們都背離了自古以來“不作田土沒飯吃”“耕讀傳家”的傳統,撕裂著鄉土上最后的道德操守。一邊是外地被用過激素的蔬菜和打過除草劑從不發霉、光亮光亮的大米,一邊是故園大片大片空置的田地。
長期的二元結構,讓故鄉的人們做夢都想變成城里人,不要作田土是人生第一大目標。凡出外打過工的人,都不會回家鄉作田土,寧愿耍,也不想作。沒有鄉鎮企業,沒有民營公司,沒地方去,就在家打牌。
走在故鄉的田土里,看著荒成一片,負罪感、憐惜感無法排遣,就像看到一碗碗白米飯倒在馬路上。雖然,沒作田土不影響他們的收入,但勤勞的人文精神已像丘丘相連的黃土地上的生芽(作物)一樣讓人看不到了。大家都跑往城鎮,田荒了、土荒了、水荒了、屋荒了,怎么辦?這種發展方式絕不是長久的,也不是我們所要看到的。解決這些問題,不是一時一地,需要每個對故鄉有感情的人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