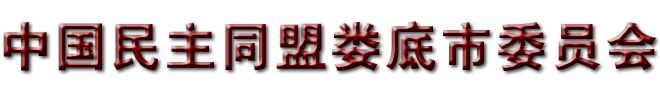想起一個人
七十歲,對于一個人,基本上等于一生;但對于一個組織,應該還是青蔥歲月。時間催老了許多東西,但永遠不會催老我們對民盟先烈那一份出自內心的敬重。
在我心中,聞一多是一面永遠的旗幟。
“初識”聞一多,是在二十五前的大學課堂里,那時我還是一個十八歲的小青年,我記得當時讀到的是他的兩首抒情短詩:《發現》和《死水》。讀那種詩,你沒法平靜下來,因為詩的情緒本身就是悲憤的,他痛恨于祖國當時政治的黑暗、民生的凋蔽,卻又似乎有些無可奈何。由于這種熾熱的赤子情懷,我對聞一多有了一份深深的尊敬。
大學畢業進入另一所大學,教的恰恰是現當代文學。在大學課堂,老師是有取舍作品的權力的,但無論現代文學課時如何縮減,也不管試題是我出還是別人出,聞一多的《太陽吟》和《死水》一定是我必講的篇章。我希望自己教給學生的不只是某一首或幾首詩的思想與藝術,而是詩中體現出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國天下的情懷。在我看來,知識分子的家國天下情懷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民族賴以前行的動力之一。
聞一多的一生確實讓人敬佩。他在西南聯大做教授時,薪水不足養活八口之家,家里能當能賣的東西都全部當完賣完了。不得已,他只好到附近的中學兼課。只教了一年,又被學校以“向學校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開除。最后他只好選擇刻印。于是,昆明市面上便出現了聞一多治印的“潤例”。在小圈子里刻印幾乎掙不到錢,聞一多急了,決定擺地攤刻印。只擺了一天,就被人勸了回來。后來,校長梅貽琦聯合11名教授在報紙上為他刊登刻印廣告,讓他在家里“設點”刻印,他的經濟條件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聞一多并沒有沉溺于對個人生存的顧念中,而是始終關注國家民族的命運。他從1943年起就勇敢地投身于民主運動的洪流,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9月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同年11月,昆明學生掀起爭民主、反內戰運動,
聞一多先生遇難已經六十多年,在這六十多年,世事不知變化了多少回,知識分子面臨的生活處境也遠比聞一多先生優越。但我覺得聞一多先生的精神并沒有過時,有兩點特別值得當代知識分子學習。
第一,關注現實、關注社會的精神。知識分子擔負著創造知識、傳播文明、參與社會道德模式和法律環境構建的重任,他們是社會最有良知、最有精神支撐力、痛感神經最發達的一部分,理應超越個人的得失,把目光投向最廣大的人群,關心他們的衣食住行,知曉他們的精神需求,做弱勢者的權利代表和精神代言人。只有大多數人生活幸福,社會才會穩定,國家才能繁榮。古人對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重要作用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有句這樣的話:“士大夫之恥,乃為國恥”,那么,士大夫之榮呢,當然也是國榮了。
第二,勇于承擔大義的精神。因為所學專業不同,個人追求相異,知識分子分為技術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兩種。所謂技術知識分子,就是執著于自己所從事的某個專業的讀書人,比如教師、醫生、科學家、律師等等。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是指的經常對老百姓關心的問題發表看法、有能力影響社會輿論甚至政府決策的讀書人,比如作家、時事評論家、思想家等。無論你屬于那種類型,有一點是我們必須引以注意的,那就是在職稱、職務、老婆、孩子、住房、鈔票這些東西之外,我們還得對社會負點責任,對國家的政治施加應該施加的影響。如果道義需要我們挺身而出,哪怕是象聞一多先生那樣犧牲生命,也應該毫不猶豫地站出來。一個只關心個人物質享受,不關注國家民族出路的知識分子,絕對不是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也不可能在專業上取得讓人銘記的成就。